编辑推荐:
本刊特邀哈佛医学院院长George Q. Daley撰文追忆诺贝尔奖得主大卫·巴尔的摩(1938-2025)的传奇生涯。通过系统梳理其逆转录酶(RT)的突破性发现、Whitehead研究所等科学机构的创建历程,以及在国际基因组编辑峰会中的伦理领导作用,全面呈现这位跨界科学家如何重塑分子生物学发展轨迹,为生物医学领域留下制度建设与科研诚信的永恒典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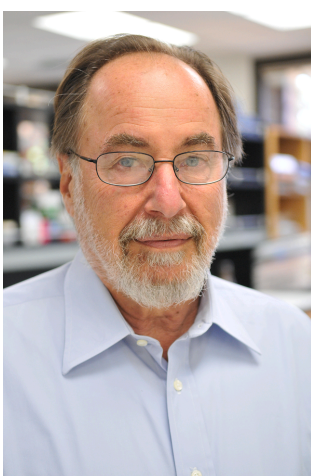
 生物通微信公众号
生物通微信公众号
生物通 版权所有